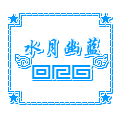文革“御笔”沉浮录(下)
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一位主笔。在他的记忆里,梁效是在毛的建议之下成立,此后,又应江青的要求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梁效也因此成为”批林批孔”运动和”儒法斗争”当中的急先锋。但是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之后,范达人发现,梁效原本忙碌的工作,忽然变得清闲下来。
清华刘冰案
解说:1974年10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筹备工作。这时,江青和王洪文向毛主席告了周总理的状,指责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独断专行。江青提出,由迟群出任教育部长,毛远新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且批评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人贵有自知之明”。
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发文件,或者其他一些大批判文章都说,说江青提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人大副委员长,现在这个真相呢,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不是江青提名,是周总理提名,毛主席给她圈掉了,我问过,问过这个谢静宜,她说主席呀,不希望我做大官,他是爱护我,那么迟群呢,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他闹情绪了,这倒是事实。他以为教育部长是他,结果没有,后来周荣鑫当了教育部长。
无论如何,梁效的直接领导者,曾经受到毛主席器重的迟群和谢静宜,被毛主席排斥在国家领导集体之外。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四届人大选举邓小平成为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负责全国工作。
四届人大后,江青等人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批评江青 “批判经验主义”的行为,并且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范达人回忆,当时江青挨批的消息并没有向梁效传达,但是他发现,不久之后,梁效就开始陷入了低潮。
范达人:那段时间就是好像是75年的六七八月份,大概这段时间,这个梁效就是清闲起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多事情干干,所以我们要求去,我提出来,我说我们去参观秦岭啊,写《秦始皇》一本书,后来他就下放我们去劳动,到乳胶厂劳动,我们也很高兴,去劳动劳动,这段时间当时为什么有低潮,我们当时不太清楚,那么事后,后来我知道这个背景,就是江青他们挨批了.迟群、谢静宜来得少了,我们外头约稿任务也少了。
解说: 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系统地全国整顿,但是毛主席没有向梁效传达过为整顿工作进行宣传的指示。
范达人:这段时间实际上我想这还是毛在掌握,毛主席在掌握,他是不是当时这段时间需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社会动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邓小平重新上台,他搞整顿,这个整顿,那个整顿,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都纠正过来了,
从五月到十月,梁效只好发表过去写好的一些稿件,然后就是到各地去参观、劳动。1976年10月,梁效成员到大寨参观,他们刚刚和大寨英雄郭凤莲说了几句话,突然就接到了迟群的紧急电话。
大寨参观途中,迟群突然来电话了,给梁效的支部书记李家宽说,立即返回,说立即返回干什么,说另有任务,要立即返回,然后我们没办法,大家立即返回了。返回立刻就开始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几名干部于是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这封信的抬头写成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希望能够通过邓小平转送给毛主席。
范大人:这个刘冰他原来是老干部,原来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他这个思想基本上是就是原来这个那个轨道,就(文革之前)17年那个轨道,路线,那么他告的主要是一些作风上的问题,霸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民主,实际上是对他们这套不满意,
解说:刘冰等人见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他们将迟群和谢静宜一并告上了中央。迟群不久就得知了消息,于是召开了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会,主要目的是批判刘冰等人的告状行为。
范达人:清华大辩论开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小范围,党委内部,然后一直扩大,扩大会,然后是全校会,集中批判这个刘冰他们就是实际上搞复旧那一套,就是恢复文化的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
面对迟群的批判,刘冰等人据理力争,并且期待着毛主席的答复能够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毛主席认为,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目的是反对毛主席本人,同时毛主席在批示中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范达人:其实毛主席这个批示很说明问题,他完全站在谢静宜和迟群这边,他说这个刘冰等人写信告这个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心里的矛头是针对我的,这个刘冰,后来我看他的回忆录,他也蒙了,我是向你反映情况,对这个迟、谢不满,怎么矛头针对你了,我是好像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会看出谢静宜跟毛的关系,因为什么呢,毛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联络员,是他的人,他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北大、清华,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梁效,他就点了邓小平,我在北京,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偏袒偏袒刘冰。
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清华,迟群和谢静宜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不断地升级,而毛主席的批示,使转呈信件的邓小平也成了批判的目标。
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不久之后,这个会议的相关文件传达给了梁效。范达人意识到,清华大学的问题,此时开始演变成又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梁效的清闲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解说: “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范达人: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梁效的作用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批林批孔初期一开始出来,可以说这次他是可以说是到了顶峰阶段。
解说:梁效在第一篇文章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目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此后,毛主席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
范达人: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我说这次这个右倾翻案风的特点,实际上我是根据当时领导的意思和报刊文章概括的,他们以为是中央哪个首长的讲话,所以后来报刊上到处有我这个东西..
解说: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 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
当时啊,广播(这篇文章)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哎哟,大过年的就把我们这文章头版头条地广播了,我很高兴,但事后看来呢,是颠倒是非,扰乱人心,那时候胡耀邦主持这个科学院的工作,号召大家搞新的长征,向科学进军,他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是根据上面的意图说他这个,这个右倾回潮,这种批判是错的.
解说: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梁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写作了大量的文章。
范达人: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
解说:1976年春,邓小平失去了主管全国工作的实际权力,他着力进行的整顿工作也被迫停止。范达人也在此时开始了解到,社会上对于梁效所写的文章反感到什么程度。
范达人:我有解放军的一个老朋友,到他家里吃饭,礼拜天,他就当着我面说,说你们又要批邓小平了,老干部都批光了,谁来工作啊,这个局面怎么维持下去呀,就是直截了地表示对我们的不满,这个事情对我有影响,我们在山西参观的时候,山西呀,参观一个钢厂,这个钢厂给我们介绍说,梁效人来参观了,介绍,他介绍介绍说,哎,本来呀,我们生产搞得很好的,批林批孔一来呀,生产往下降了,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们梁效是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啊,你在我们的面前就骂起批林批孔来了好像,说我们的坏话了,可是他讲的是真话,
解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同年的清明节,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梁效成员周一良和钟哲民也在其中。但是当天下午,这场群众纪念活动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4月5号下午,毛通过毛远新传达了他的批示。批示当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之后,天安门事件就被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目的是“妄图扭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4月7号,根据毛的提议,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解说: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
文章发表后,又成为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最强音。但在这时,范达人思想上也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梁效写作的文章可能不仅仅是贯彻毛主席思想这么简单。
范达人: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
但人家觉得很奇怪,范达人在梁效红得发紫。 是吧。这个好像是很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很出风头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国庆宴会都有他的,是个主力,他为什么要离开梁效,就是这些因素。
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主席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9月,在等待调职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参与写作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梁效由原来的毛思想的诠释者,一夜之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解说:这是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
范达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
解说: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范达人记得,在毛主席追悼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文章里,按既定方针办,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当时留给他很深刻的印象。
范达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
解说: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
范达人: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
解说:范达人的写作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校样,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 日。
范达人:10月1号,就是乔冠华的发言,送到华国锋那,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对原来的那个好像毛主席的词,哎哟,不对呀,6个字差了3个字,毛主席不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是说照过去方针办,所以他批了一下,说6个字错了3个字,以后不要讲了。张春桥又把它压下了。
解说:此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们和梁效的成员对于当时中央高层对这六个字的争论毫不知情。于是《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 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
范达人: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
解说: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梁效结束
1976年10月6号,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华国锋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把四人帮一网打尽。范达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消息灵通的其实人士都已经开始庆祝“四人帮”的覆灭了,但是当时他自己还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
范达人:我这个很迟钝,他是,我后来知道10月6号好像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可是我到10月10号我还不知道,10月10号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叫做刘隆亨,他碰见我了,他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我还是聪明了一句,反问了一句,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哎哟,我心里一震,我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解说:范达人将迟谢被捕的消息传达给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范达人: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
解说: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范达人:给我很多警告,说你呀,你现在还不交代,你不要以为没有事了,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后悔晚矣,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我不能瞎编啊,编了以后,那怎么办,编了以后你要自圆其说,是不是,后来我说听天由命,随他去,
解说:于是,范达人成为从严处理的典型。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
范达人:上了囚车以后,我想看看…,不让我看,坐下去,坐下去,让我坐在地下,押到一个地方,然后出来以后,出来以后铁门一道一道打开进去,一道一道打开,这个阴森森的,然后他们大概没商量好我押在什么地方,说你在这边等一等,正好有一个犯人在那打扫卫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说这里是半步桥监狱,半步桥监狱,真把我关进监狱了,我说,这个半步桥监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参观过,1956年的时候我参观过,我说,真是,这命运真是捉弄人啊,1956年我来参观过,这个多少年以后吧,1977年,十多年以后,我在这蹲狱,
给我关进来以后,给我扔进来两条被子,这个两边犯人一看,哎哟,哎呀,新被啊,真好啊,但是被子上写个囚,囚被,他们说很好,他们觉得对我很优待,我心里凉了半截,哎呀,我说真的成了囚犯
解说:范达人未经审判就成为了囚犯,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刑期到底会有多长。
范达人:如果告诉我关一年啊,我很轻松愉快地呆在那,熬他一年,比较平静的,它是茫茫的一片黑夜,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也可能关死在那儿,也可能把你干掉,因为这个罪名太重要了,你篡党夺权动员令的执笔者,或者炮制者或者什么,你不承认,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真是一片漆黑,完全是心灰意懒,
解说: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8年秋,范达人在监狱的报纸上看到了出狱的希望。
范达人:当时这个监狱里头啊,它有《人民日报》,每天给份《人民日报》,我有时候看看《人民日报》的大标题,看看一些消息,我看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有些变化,比较强调实事求是,比较强调落实政策。胡耀邦当时就说,把这个阶级斗争看作是路线斗争,不是这个革命与反革命这种斗争,另外他树了个彪炳,说辽宁省委书记叫李伯秋吧,他说这样的人,不要关起来,可以放出来。有这么个彪炳,这个我也就于是就放出来了。
解说: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范达人看来,这个结论给了他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机会。
范达人:就是北大党委,给我们下达一个结论,初步结论,他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我们当时听了很高兴。
解说:尽管北大党委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梁效的问题并未获得彻底的解决。此后的十年里,梁效的成员先后几次接受审查,结论也不断变化。范达人此时已经恢复了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文革结束开始,他不断地反思自己曾经作为御用文人的经历。
范达人: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了宣传某一个政策、方针,他需要人,组织人来宣传政策,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以后也会有,所以这个现象不会消失的,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知识分子啊,应该,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个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把自己呀,经过大脑思考的,认为正确的东西表达出来,认为不好的东西进行抨击。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
文革当中,梁效不是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罗思鼎,还有唐晓文,初澜,池恒等等。有学者认为说,深入研究梁效、罗斯鼎等等一系列的 “文革遗产”,其实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对于梁效历史的回忆,其实一直心情都十分复杂。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 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