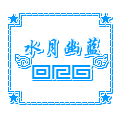血案导演:中国的屠夫们
中国历史本来的核心部分之一,便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大屠杀。但用文字成就的中国历史,成为“吾皇万岁万万岁”的“起居注”、宣讲文治武功的替代品。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斑斑血迹、不绝的冤魂,成了被专制者豢养起来的御用史学家,用尽文字功夫要来掩盖的历史真相。但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已经加以掩盖、遭遇历代史家百般阉割的二十四史里,关于屠杀的史料钩稽出来,绝对骇人听闻。如果不研究中国为何诞生如此多的大屠杀,便不能真正理解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中国,因为屠杀、血案、吃人是中国历史的中心词。
中国自古生存环境艰难,为了争夺人力资源资和广阔的土地资源,永久占领有利地位,战争频密不断。战争中将俘虏掠为奴隶,虽也此生劳碌命苦、食不果腹,但算得上俘虏中的幸运者了,像秦将白起为了避免赵卒为乱,竟坑杀已投降的赵国士兵四十万,这是中国历史有数的真正的大屠杀。虽然古代的战争没有今日之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也有一系列的规则,因此“赵人大震”。到了秦始皇,便杀掉四百六十位儒生,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不按照他的旨意耍笔杆子,在焚掉大部分让人不放心的、惑乱人们思想,不能统一思想的著作后,便来消灭这些有解释惑乱人们思想书籍权利的人,开了后世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灭思想拥有者和阐释者的先河。张献忠把士子征来考试,却趁机杀掉他们及其家属。康、雍、乾时代是用文字狱的方式来消灭肉体,凌迟处死、满门抄斩等,如此一来,一个人有胆敢独立思考便成了一种灾难。而不幸的是,这种灾难,不仅存在于国民党时代,在四九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更是登峰造极,很多有思想的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思想、政见异端而遭杀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只不过是其间现在的人们尚有些许记忆的显例罢了。而更多死于非命的知识分子何止成千上万,从我所搜集的众多右派言论及批判右派的言论,以及在各个时期遭受的残酷批斗,包括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省不予改正的右派的非正常死亡来看,可以说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大面积消灭思想拥有者和阐释者最为厉害的一次,可谓惨况空前。而这样大规模导演思想杀戮和身体消灭的导演,便是和专制制度一样的一党独裁,其间主导设计者,无疑是擅长于搞阳谋、引蛇出洞的毛泽东。
四九年的政权与历代农民起义名异而实同,所以在当政者获得政权后,便不惜御用一大批史学家包括其它人文社科学者,对历代农民起义极尽赞美之能事。把那些所有涉及的大屠杀说成是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好像这些被贴农民标签的起义者,要杀人之前先看看背上写没写有“地主阶级”标签,才最后定夺是否杀他似的。既然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对抗地主阶级,是为了天下百姓,好比“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为什么所有农民起义不成功则罢,成功夺取政权、获得王位后,会比以其它方式夺取政权者更加残酷暴戾呢?那些均平富的口号、天父兄弟的称呼、“为人民服务” 的幌子,所代表的实际利益哪去了呢?已经被所谓的农民起义的流氓领袖们独断专有了,哪里还有你细民百姓的份呢?正如张养浩在元曲《山坡羊》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意味深长的是,官方近几年对农民起义研究的冷淡,不再那么赞美,并非真正学理上理智思考的结果,而是害怕对农民起义的赞美和宣传,导致新一轮对他们一党独裁的反叛和起义,真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作为所谓的农民起义政权,其实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自秦朝以后的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在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 (《从韦小宝说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张献忠这种从小队长起家的“农民起义无领袖”的残酷歹毒不必论了吧,最终称王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尚未登极以前,便率军队以吃人肉上瘾:“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之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之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尚未登极时就能如此“为人民服务”,让士兵吃得“想肉”,登极后更加“为人民服务” 则是必然的,为了惩治人民的敌人,处罚贪官,“明太祖亚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草木子》)把实草的人皮悬在官员的办公室,真是残酷得有想像力,但这样真的能“为人民服务”吗?或许能为搞死人民服务吧。事实证明,一朝一代、一党一派的独裁统治是任何办法都无法使其长治久安的。
朱明王朝有如此“为人民服务” 的开国皇帝,便有将“人民的敌人”方孝儒、铁弦、景清“剥皮揎草”明成祖朱棣,不特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发展处理敌我矛盾高明办法,譬如将忠于他侄子建文帝的方孝儒诛连九族,杀掉一大家族大几百人,这样还不过瘾,还要把方孝儒等人的妻女弄到军营里“改造思想”兼“改造肉体”,让士兵轮奸以“帮助”她们生出 “小龟子我“和“淫贱材儿”。当然,要找像这样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并不困难的,无论是别人要杀他老爸他却要分一杯羹的刘邦,还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的黄巢,都是了不起的古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于太平军的洪秀全简直就是革命的化身,他领导的起义实在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具有指路明灯的性质。洪秀全革命功夫不错,读书却不大在行,从14岁至30岁考四次秀才均已失败而告终,因此一旦在南京登基,便下令凡是通文墨者不来考试便斩首不留——对比只任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在四九年问鼎后便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宣布为战犯,包括后来大整特整知识分子,骟掉精神,消灭肉体,真是渊源有自,活学活用,真是个好学生。至于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政敌杨秀清全家及亲信六千余人,而且两个月里总共杀了各种文武官员二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不愧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啊。只有伟大的领袖,才能干出超出我们想像、让我们小民百姓都随时都发抖的伟大事业来。
中国盛产制造血案的屠夫,其根源在于家天下(一党独裁)、靠血腥屠戮、战争杀伐来进行政权更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背后的哲学理念便是无穷无尽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只不过是把人文社会和自然界来个翻天覆地大斗争,重新按独裁的意愿洗牌而已。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自然没有宽容精神,视异见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这种流血杀戮式的政权更替,和靠选票来平和、平稳进行政权更替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制度能比专制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合作,争取双赢。换言之,一个人的存在,不以消灭他人身体、钳制他人思想为鹄的。而专制制度则往往对政治和思想异见者痛下毒手,因为这些异见,戳穿了专制者所玩乐的“皇帝的新衣”的把戏,同时也揭穿了他们独霸利益,却以极高的道德来号召普通民众牺牲和忍让的伎俩。此点在历代的专制皇帝包括像张献忠这样短命的割据政权的人主身,都极其残酷屠杀思想的异己者。把异己者消灭或者使异己者钳口后,专制独裁者就更加为所欲为地愚弄老百姓,更加大规模地屠杀或饿死无辜民众。如此一来,短暂的统治历程充满了血腥,而且在表面上显得像一块铁板一样稳定,但铁板之下便是另一拨以生命作为赌搏的人,对专制者又一轮的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循环往复而不休,便使整个中国进入专制制度奴役的怪圈,以至于一些头脑糊涂而简单的人,好像被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奴役得很舒服了,得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的荒谬结论。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兹的小说《无形命运》,借用小孩子之口反应希特勒时期的大屠杀。由于“他对弱小的个人对抗野蛮强权经历的深刻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比之下,我们国内那些发烧的诺贝尔追慕者,对中国现实的苦痛、流血、屠杀显得多么漠不关心,只能成天做得诺奖的白日梦,便势所必然。当我上网用“大屠杀”三个字进行查询,有关网页八十一页,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屠杀、现当代中国大屠杀的寥若辰星,仿佛这些惊天大血案不曾发生过一样。有“关于大屠杀文学”、“关于大屠杀常见问题”、“大屠杀档案”等之类的英文网站及英文链接。但却没有一个中文方面关于“大屠杀”的系统网页。不特是十五年前的六--四大屠杀没有丝毫的展示,即便有也被官方的网警阻隔在读者能阅读之外——这种对于屠杀真相的掩盖,一方面显示屠杀者对于真相的恐惧和心虚,另一方面也是愚民之必须,把谎话重复千遍,好让其变成真理——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诸方面的历史真相,也研究得非常肤浅,这对一个鲜活的个人和苦难的民族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记忆缺失。
让我们记住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屠夫们,把他们所犯的滔天大罪,昭示天下,针对现实,警醒来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部材料翔实、议论缜密的《中国大屠杀史》问世,以告慰自古及今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屈死的冤魂。同时,要防治历史及现实中多次暴发的大屠杀再次发生,只有抛弃一党独裁及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提倡宽容和解,通过非流血的社会改良,实现社会制度的慢慢变革,以使中国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迈进。否则,大屠杀终究不可避免,血流成河的残酷现实必将会再度出现,这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妓女。此语虽刻薄,却也极其真实。今年是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但如果走上街头询问普通的成都市民,却没有几个人记得这个日子。中国的历史太悠久,“遗忘”也许是“生存”的前提。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谁是指挥了那场屠杀的屠夫?那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在天府之国这块物宝天华的土地上,生命像稻草一样茂盛,时光却都消耗到喧嚣的麻将桌上。
三百六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浸透了鲜血,空气中飘荡桌腐败的尸体的臭味。所有的房屋都空了,所有的田地都荒了,“扬一益二”的成都重新回到了史前时代。修建了都江堰的蜀守李冰,没有料到成都会遭受这样的惨剧;用华美的文字来讴歌家乡的司马相如,也没有料到死亡会笼罩这片世外桃源。即便是饱经战乱的杜甫和仕途坎坷的苏东坡,也难以想象他们所爱的土地会变成人间地狱、他们所爱的乡亲会成为刀下亡魂。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伟大领袖”究竟对人民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吾友冉云飞学识渊博,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例如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后鉴录》提及屠成都及其州县事:“(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面对这样的史料,秉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物史观”来撰写中国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则统统斥之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侮蔑”。然而,我在家谱中发现,母亲这一家族乃是源于“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我想,这样的事实总不是谁能够的杜撰吧。
张献忠的“由魔成圣”,说明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凭借杀人之多而成为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传统,即“屠夫崇拜”。鲁迅是最早发现这一杀人和吃人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鲁迅最厌恶的人是谁呢?大概许多鲁迅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鲁迅最厌恶的人就是张献忠。鲁迅在写到这个屠夫的时候,用的是最为尖锐的语气和最为痛恨的情绪。鲁迅看重每一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因此他万万不能原谅像张献忠这样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的屠夫。与鲁迅恰恰相反,与张献忠最为“惺惺相惜”的人是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就是吸取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维方式的、推陈出新了的“张献忠”。鲁迅痛斥张献忠,而毛泽东却欣赏张献忠,这一细节说明了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根本的差异。所以,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是一句谎言,这种说法只能欺骗一些单纯的文人。
有人认为屠夫至少还有一个值得羡慕的品格,那就是“勇敢”。但我认为,屠夫不是勇士,屠夫的另一面乃是懦夫。真的勇士,乃是谭嗣同、秋瑾、张自忠、遇罗克、林昭等人,他们或为同胞之解放而断头,或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战死疆场,或为求索真理而献身。真的勇士,乃是像殷海光这样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如林毓生教授所论:“殷先生言行的意义在于:在一般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条件下,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具有的责任感的召唤,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为原动力,硬要参与政治过程所发挥的政治性影响。殷先生说:‘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 当时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论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对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却逆流而行。”这才是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勇。与之相反,屠夫们在骨子里都是懦夫,他们背离真理并摧残真理,他们并非挑战强权而专门屠戮妇婴,他们出于恐惧和猜忌而实施他们那邪恶的屠杀计划,最后他们自己也走向了偏执狂和精神分裂。我们今天很难读到关于张献忠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史料,但却能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发现关于毛泽东病态心理的详细描述。屠夫们最恐惧的便是众叛亲离,屠夫们最后的命运却无一例外都是众叛亲离。他们本该在疯人院中被治疗,却不幸地掌握了毁灭同类的权力。
中共建政以来,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与作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衍生出一套虚幻的“农民起义创造历史”的乌托邦(当然,与其说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流氓无赖之党”,因为它依靠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却对农民实施了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恶毒的统治)。毛泽东喜欢阅读《水浒传》,因为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镜子,中共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其实,从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到毛泽东,都一样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无赖,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成者为王败者寇”而已。当然,毛泽东是这一历史人物序列中最伟大的“红太阳”,而张献忠也俨然成为一个不可以批评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战友”。张献忠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素养不深,兵力有限、控制区域也有限,所以他的杀戮主要还是集中在四川及其相邻省份。而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以“继续革命”为屠杀的理论基础,以现代国家机器为屠杀的工具,其杀人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效率之高,都让张献忠望尘莫及。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中国的“屠夫崇拜”变本加厉。近期《新京报》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伟人纪念商品京城热销”的专题报道,记者林文龙写道——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读者留言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永久纪念,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将是我们的传家宝。北京图书大厦企业策划中心工作人员刘艳告诉记者,因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掀起的“纪念商品热”并未随纪念活动的结束而低迷,上周六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的首发式上,短短一小时内就签售了近百本,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全书共三十六页金纸制成,每套标价一万八千六百元,上市前就备受关注,自三月十一日正式发售以来,短短二十天内即卖出一百二十二套,这一记录刷新了北京图书大厦精品图书的销售码洋纪录。热销的除了图书外,还有音像制品。据大世界音像副总经理郭丰录介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退出的大型文献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VCD一上市就大受欢迎,现已卖出一百多套。
这段文字让我毛骨悚然。在西方,最黑暗的年代就是对屠杀保持沉默的年代;而在中国,对暴行的沉默却成了“道德高线”,因为大部分人都成为屠夫的真心实意或三心二意的帮忙与帮凶。直到今天,在中国对屠杀的肯定和对屠夫的赞美都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教授和博士这样的知识精英。新老左派虽然互相攻击,却共奉毛泽东为邪教教主。某些学者文士虽以“后现代”的西装革履出现,却怡然自得地与屠夫一起茹毛饮血。近年来,中共外交部多次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己却对毛泽东这个比日本战犯们还要暴虐的屠夫顶礼膜拜,难怪日方从来就不理会中共那有气无力的抗议。在西方,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喊冤叫屈,无异于对抗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而在中国,张献忠依然像游鱼般逍遥于历史教科书之中,毛泽东的头像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他的子民继续遭受屠杀。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重大差异。
思想家鲍曼致力于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产生的背景:“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当把人定义为“非人”的之后,屠杀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张献忠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读书人都不是人,而是猪、狗、羊;在毛泽东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反革命”都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属于这个“新社会”。屠夫蔑视爱、同情和悲悯这些高贵的价值。那么,人类有没有希望从仇恨和杀戮中解脱出来呢?鲍曼不接受“以屠杀始、以屠杀终”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黯淡的预测,他认为人内在的耻辱感可以将人类从屠杀中解放出来:“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沦为囚徒的潜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发现了人类摆脱屠杀、对抗屠夫的一线希望:“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还是属于张献忠和毛泽东们,屠夫们依然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应该选择“这一个”选择,尽管我们会成为屠杀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是制止屠杀、击败屠夫的唯一办法。我们不能乞求屠夫突然大发善心放过我们,我们也不能祈求天国突然降临人间而自己什么也不做。今天,我们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乃是要追悼那些沦为孤魂野鬼的同胞,乃是要将张献忠这样的屠夫从“先贤祠”移入“西湖跪像”。让英雄享有英雄的荣誉,让屠夫接受屠夫的审判,中国人才能彻底告别被屠杀的命运。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