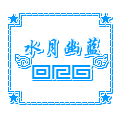悠悠五千年,堂堂大中国,国粹自然是不少的。如果我说喜欢搞屠杀才是中国真正的国粹,希望你手下留情,不要把我当祭品来完成这个伟大国粹的证明,因为我的脑袋毕竟不是让你拿来切了可以再生的韭菜。我虽对现今强势者把鲁迅奉为不可批评的神祗、不容非难的权威,一向是反感的,但对迅翁说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吃人,还是相当佩服的,因为这算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拿住了中国历史的七寸,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底细。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形成里本来就把杀人,包括强权者搞大屠杀,当作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制度设计来让人们潜移默化的遵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肉弱强食的、赤裸裸的生物博弈。从升斗小民、斗宵小民、市井细民、一介草民的称呼里,已然透露出老百姓蝼蚁一样的微贱下场,遑论有何尊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最不值钱的便是大众的个体生命。以至到了现代社会,还有这样视人命为儿戏的领导人,说什么“中国死三亿,还有一半的人口,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便是中国残酷的现实。建立在对大众个体生命的蔑视之上的文化和制度设计,当底层的人完全无法活命的时候,就会常常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向强权者挑战的博弈武器,来个鱼死网破,这便是中国史学研究者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
中国为什么喜欢杀人?
平日读中国历史,注意到人命微贱不如蝼蚁的事实,总是令人废书浩叹。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非制度学派至高无上的推崇者,但掩卷长思,认真比对,的确深感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以及文化中对等级制度的崇奉,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中国成为世界人权重灾区的根本原因。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是免不了血腥剿灭的大屠杀的,同时因战乱而带来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死尸枕籍,即便是同一朝代之间的皇帝更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代皇帝对父皇的相关宠幸人物,也是免不了屠戮杖打、流放贬谪的,由此也难免伤及不少无辜。要言之,无论是开国之君、中兴之主,还是守成之君,大多脱不了某些共同之处,即残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独断、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作为专制制度这个金字塔式制度的最高体现者,皇帝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志,从他身上无疑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缩影。
一般说来,无论是古代的皇权专制还是现代的一党独裁,几千年中国政治的核心便是流血政治,流血政治的核心便是用“二杆子”起家。川人所谓“二杆子”,指莽撞、鲁莽、技艺不精的半吊子,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这些技艺不精的二吊子便统治了几千年,四川人常用的“二杆子”实在是我总结出的中国历代政治统治术之“二杆子”的绝妙比喻。而我所指的“二杆子”便是指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于征服和治理天下者,真是缺一不可。笔杆子颠倒黑白、为我所用的功夫,实在是征服天下和牧民治国最需要的招数。从习纵横之术、勾距之术的谋士说客,运筹帷幄、传檄而天下定的军师,到独尊儒术、愚民洗脑的辅臣,无不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和专制制度的要求,用笔杆子来精神上实施“杀人之术”,从而达到为人主所用,使愚民黔首俯首贴耳,至于那些剩下一些不大顺从的反对派,则会用尽各种方法,或隐蔽或公开地让他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谋反窃国之始、逐鹿中原之时,从鱼腹藏书以及各种各样的装神弄鬼,到大言欺世的讨伐文章,都是为了自己争霸天下造势,为自己谋反找到可以煽惑人心的支撑点。因为一朝一代是一姓的私产,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是一朝一姓之天下,但刻酷的皇帝在谋臣的牧民之术的教导下,是绝对不会把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拿来当作号召人民臣服的理由的,它必然敷上一层道德膏药——即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不折不扣的正统继承者,是中国最高道德的化身,哪怕残酷歹毒到极点,他也是以德治国的。如此一来,便把血腥得天下,残酷治天下的事实“圣化”了。这种“圣化”功夫便是历来谋臣宰辅爱帮主治搞些“以德治国”的正统论。
正统论主宰着中国人的历史视野以及政治判断,以至许多令人敬仰的大学者频频迷失在正统论的泥坑里而不自知。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尊刘抑曹,其尊刘氏为正统的满腔热忱,溢诸纸墨,露骨至极,开后世各种民间文艺里曹操阴险狡诈、篡谋刘氏正统之先河。从《春秋》序主宾、明正闰起,中国关于正统的议论,以及对正统尊奉的言论,可谓史不绝书。当今史学重镇饶宗颐先生为时五年,“淹贯乙部,旁通别集”,搜罗殆尽,成史论和史料都为一集,洋洋大观,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而赞同正统于朝代更替之更要者,不知凡几。这说明正统论作为一种史不绝书的洗脑手段,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不用怀疑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古代有多么伟大的市场。这也就变向证明了,古代的笔杆子们在帮助皇帝夺取天下,洗去人们仅有的一点怀疑精神方面,做得是多么到位。这就反证了皇帝及其所属的专制制度对笔杆子的倚重程度。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正统也者,无非是“成王败寇”的俗烂翻版而已。但在旧时,连史学巨擘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脱不了对正统的迷信和维护之中,倒是为了篡谋秦政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要赤裸而深刻些。
笔杆子虽然重要,但只靠纸上呐喊和口水功夫,毕竟不能解决嗜血成性、尚武争胜的对手,因为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因为你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和随机应变的谋略后,才能达到的上佳境界,非寻常人物和普通的实力,所能够梦见。所以中国从来都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用主义哲学,而开国之君便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不折不扣的实践者,泛览古今中国历史,概莫例外。如果争天下时用“笔杆子”,是要假借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来麻痹老百姓、号召跟随者、打击敌对势力,那么“枪杆子”则是图霸业之必须的利器,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问鼎中原,雄霸天下,绝对是痴人说梦。因此不择一切手段以争得天下——像宋襄公一样的妇人之仁是被千百年来“还看今朝”的皇帝嘲笑的对象——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赚得自己的江山,便成了创业之主的共同爱好。一旦问鼎成功,即有谋臣贡献“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样就把枪杆子和笔杆子彼此之间不同但互相弥补的功效,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驭民之术,固然洋洋大观,但核心的方法无非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枪杆子是实力的体现,哪怕你是个十足的流氓——事实上中国历史由流氓而皇帝者不乏其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谋臣和史家也要把你当作正统来供奉,并且不惜一切力量来保卫你异于常人的高贵性。枪杆子固是实力的体现和政权稳定之保证,但枪杆子带有相当的后锉力,用不好,便会丧及自身,因此“杯酒释兵权”、“狡兔死、走狗烹、良弓藏”这样的事件屡屡上演不衰。不特如此,持枪者必须经御用之笔杆子,将脑袋洗得干干净净——发展到现在便是党指挥枪,而非军队国家化——以便毫无二心地效忠皇帝所把持之政权。笔杆子的伟力及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决定枪杆子的方向,刚才对准张三的枪口,可以经过洗脑,完全调转头来对准李四。笔杆子洗脑的最高境界便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军队,正所谓传檄而天下定。古代的正统论、真命天子,现代的“一切为了人民”,都是洗脑的惯用伎俩,有绝顶的煽惑功用,屡试不爽。可见在不择手段时,不必事事都搞什么劳什子创新。
不过,千万不要认为笔杆子就会使枪杆子俯首听命,关键在人主对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关系的巧妙运用。有强大枪杆子作为国家统治的机器,不愁笔杆子不听话地写那些洗尽天下苍生脑的谀主文章。收拾笔杆子的方式,像贾谊一样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听苍生听鬼神”,就算对笔杆子最温柔的处理手段了,只不过对你冷淡了点而已,看来没什么必要呼天抢地。最为厉害的收拾,便是捕风捉影地搞“文字狱”了。三千年文祸,为害之惨烈,绝非言语所能尽述。司马迁之遭宫刑,去掉大势,只是其显例而已。而至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的康雍乾时代,文祸更为酷密。号称“十全老人” 的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口头上提倡“胖子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其所兴文字狱实在是前无古人,持续40年的文字狱,冤案130起,由此屠杀大量无辜平民百姓,就连说胡话的疯子也不放过。正因如此,才有靠笔杆子纪晓岚等编《四库全书》以毁中国文化的“壮举”,而笔杆子若不从,则有杀、关、杖、流等手段惩治你,没有谁不惧怕三分。如此一来,笔杆子只好反过来对专制独裁者利用枪杆子而采用的酷刑,造成的人间灾难,阿谀歌颂、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美化其文治武功,便形成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血腥结合,从而达到奴役民众、损害人权,使专制制度得以长期以各种方式像幽灵一样,逡巡漫延在广大的中国,至今不散而为害甚烈。
枪杆子消灭肉体,笔杆子杀人精神,这便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两大核心武器,也是任何自称正统实则只不过游民甚至是流氓,借以起家谋反,获得天下,进而“高贵”起来的皇帝,必须的两大利器,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里——皇权专制和一党专制——都是屡见不鲜的招数。不特如此,这种经流血而非选票更替的政治,是天然的杀人温床,并且是产生杀人魔王的无边土壤。正因如此,我敢肯定地说,中国是个杀人的国度,而且杀人上瘾的人不在少数,只要他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流氓领袖的经典课程
中国几千年来,几乎无年无灾荒,以至于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清代学者秦蕙田一语中的地指出“名为备荒,实则加赋而已!”(《五礼通考》。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灾后补救政策不外乎安辑、蠲除、放贷、节约。繁役时加,不知存恤。我们从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里不难侦知中国生计之艰,灾难危难之频,苛捐杂税之繁、历代为官者之酷,实是促成中国几千年来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之中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切无不原于皇权天下和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所带来的灾难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一个朝代一旦气数将尽,就像一位病人百病缠身,纷至沓来的亡国之事齐聚一起,以至我们很难完全知晓压垮一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究竟是哪一根?以大屠杀开启朝代之始的朱明王朝,到了崇祯一朝实在是内外交困:边患四起尤其是满族人在关外的崛起,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吏治腐败、宦祸公行已使明朝不堪重负;民生凋敝、饿殍载道,使明朝成一堆洒上油的干柴。既有大面积一点即燃的干柴垛,那么中国从来都不缺点柴人,这些点柴人中最著名的便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无业游民或者下层地痞。说来也是,一个政府一个朝代让老百姓穷到一无所有,生存无方,只有拿命来最后一搏。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拿最后的本钱——生命来一次大赌博。如此一来,陈胜、吴广之徒、李自成、张献忠之辈便代不乏人,虽然我不赞成暴力革命,但这也是他们求得自存的生存权之唯一办法和方式,因为强势者不愿意拿出诚意和具体行动来对弱势者,进行适当的补尝。而强势者自古及今都有一个错误判断便是弱势者不成气候,在与他们的对垒和抗争中没有议价和叫板能力,因为强势者很少考虑弱势者亮出最后一张赌搏的底牌:生命,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由此一来,社会动荡、改朝换代之频繁、各种流氓皇帝轮番表演,史不绝载,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吃完榆树皮,接着便是人相食的地步,正是陕西的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灭亡明朝最厉害的主角——李自成、张献忠等悉数登场。
从“摇黄十三家”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是从陕西起事,而就近入蜀流窜作案的。不过李自成后来更转向北地而逼进北京,让中了反间计、凌迟忠臣袁崇焕的崇祯皇帝也来个上吊自尽。而张献忠除了少数年份外,大部时间的作案地方都在蜀楚两地来回,而尤以蜀地为其搜刮中心,杀人放火,在蜀地倍于他地。四川民间曾有个说法是张献忠在蜀楚交界地大便,他伸手扯了四川这边的叶子,遇着荨麻叶,把他屁眼给荨了,痛了很久才愈,所以他到了四川便大开杀戒。从这个故事来看,与其说乱杀人是因为张献忠变态,毋宁说是川人善谑的活证据。我也一直在想,张献忠为什么喜欢驰骋四川并滥杀无辜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明朝的守将之间的互不合作,加以大臣杨嗣昌本是楚人(长沙人),他的讨贼策略便是,先将蜀军中善战者调至湖北湖南打击张献忠,趁四川守城薄弱,有意将寇贼张献忠等追逼至四川,借刀杀人,而报其大捷之功。关于此点,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得最为入骨:“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入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入,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疲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明代史》,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这个杨嗣昌自以为驱贼入蜀而易于剿灭,真是无知之妄见。他哪知古训即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道理,四川历来出偏安一隅的地方王朝,这说明驱贼进去实足以养痈为患,让其坐大而不易消灭。以至后来张献忠部再返武陵时将杨嗣昌七世祖坟尽掘,且焚他夫妇的灵柩,虽堪怜悯,但总体上可说是对愚蠢且自以为是者的报应。
张献忠杀人如麻,当然并非他独嗜,诸多杀人方法也并非全系他首创,很多不过是对前人的借鉴而已,但照历史记载,他似乎有将诸多杀人方法总其成的味道。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杀人的方式常见的有九大类:斩杀;草杀:即挨家挨户杀;天杀:即在朝会时,放狗于诸宫,凡被狗闻过的人,即拖出杀掉;生剥人皮法;匏奴:割手足;边地:分夹脊;雪鳅:“枪其背于空中”;贯戏:“以火城围灸小儿”;其它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等。斩杀等虽也残酷,但不带有张献忠自创性质,不过草杀、天杀、贯戏、张人皮以悬市,却明显带有张献忠作为屠夫的创造性。
民间咒人或者赌血咒时常说:断子绝孙、全家死绝。其实咒是咒不绝的,哪怕他是法力无边的巫师,只有像张献忠所泡制的“草杀”才是真正的“全家死绝”。当然,如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来搞大规模的类似群众运动的“草杀”,那么张献忠就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转战川内各地,使各地生灵皆受涂炭。如果说“草杀”是干净利落的“全家死绝”,那么“以火围炙小儿”的贯戏,则是将杀人当成一门可以欣赏的、可耻而残酷的“行为艺术”,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也施行此种酷刑,在每个字缝里都沾满无辜血迹的中国史书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张献忠的杀人疯狂、变态到了何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而狗闻过即杀掉的“天杀”,其祸从天降的随机性,没有道理,没有规律,让每一个生活在张献忠周围的人,朝不保夕。如此提心吊胆,日夜恐惧,防不胜防,没有谁能够通过人力幸免,除了身体之可能被消灭,还有精神上的彻底投降,以至于就此被吓死。将人拿来剥皮,绝非张献忠的英明发明,他造反的主子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剥人皮方面就极有创造力(终有明一朝很有几任皇帝在剥人皮方面都有独得之秘),所谓“剥皮楦草”便是把活生生的人剥了皮填塞上草,以充人形。而像张献忠更上层楼,将上千张人皮挂在皇城(今天府广场)前,迎风舞动,活像上千个人上吊于此,以惩抵抗者、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其残忍凄厉,刻酷歹毒,何可言说?!
看了以上张献忠的“杀人创举”,或许有人会说他真是惨无人道,黑暗无边,其实这是他残忍之一斑而已。张献忠和大多数专制帝王和偏安一隅的小政权首领一样,多疑猜忌,拥有对普通民众生杀予夺的大权,却自己也常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和曹操梦中杀人一样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儿子残忍地杀掉后,又在第二天后悔,质问他身边的那些人,为什么当时你们不劝我?劝你?这不是废话么,你身边的人有多少颗脑袋啊,你以为别人的脑袋是韭菜么!不特如此,由于张献忠烧、杀、抢、掠的“四光政策”,使得大批人要么死亡,要么逃亡,肥沃的良田无人耕种(军队以“四光政策”为日课,故无心无力种田自给),因此在成都建立政权不到三年便自断后路,几十万大军无粮果腹。而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至于说到张献忠杀人的数量,历来是个疑难问题,可以说无论怎么研究,也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综合各种记载,大致有如下说法,可资参考。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里载有张献忠在一年零五个月中,每日杀一二百,累计杀人就是十万。当然关于张献忠的杀人记录,各种文献是互相多有抵触,这当然也比较正常。一是张之杀人,他不可能统计,自然他人的统计也不可能准确,何况彼时对人口之数核实误差还很大。二是有夸张的成份。记录张献忠杀人者,多对张之杀人持批评之说,难免有些辗转稗败的耳食之言。但当今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说所有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言论全是地主阶级的诬蔑,不足为凭。不过,关键是,以前的人没有地主阶级和农民这样头脑简单的阶级分类,他们只知道滥杀无辜是没有人性的,不像这些如今的“史学家”们丧失起码的人性判断。固然我们同情穷得不能得一饭之饱的农民,也理解不少人是拿生命作为最后的生存赌搏资本,但这一切却不能拿来作为滥杀无辜的口实。所以为张献忠这样滥杀无辜曲为回护,不仅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智判断,而且丧失了作为人起码的人道底线。
作为对张献忠杀人事实的基本判断,我认为毛奇龄在《后鉴录》里提及的屠杀成都及州县的人数,的确有夸张到不符合实际之嫌。张献忠固然兵分四路在成都周围的州县搞挨家挨户的“草杀”,却不能杀出没有的人来。据明万历年间的估算,四川的人口在310万,全国人中口6000万,就算古时官方无法像今日一样较为准确的统计,遗漏不少,如四川有400万,全国人口 7000万,也不会杀出毛奇龄所记载的那么多人出来:“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共69948万,即6.9948亿,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与此同时,《明史》里提及张献忠总共杀人6万万有奇,6万万当然就是6亿。这让批评张献忠滥杀无辜者滥杀无辜者深感困惑,同时也为那叶公好“农”的“政策传声筒”似的学者,提供了全盘否定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人类空前的一场灾难的藉口。查《词源》里对“億”引古书里的一种解释:“億之数有大小二法:其小数以十为等,十万为億,十億为兆也;其大数以万为等,万至万,是万万为億。”如果《明史》中之记载是将此前他本中的“六億”直接转误为了6万万的话,那么其中张之杀人在逻辑上最为合理的数字则应用“十万为億”的说法,便是60万。即张献忠所杀四川人口占百分之十几,而其余近百分之八十(因为四川尚有小部分人留存下来),为其他军队所杀,包括瘟疫、饿死、逃跑等。这是我与流沙河先生探讨此问题时,流沙河先生的一种推断,未敢必以为是,但沙河先生的功劳是不敢掠美的,特记于此,以备将来作进一步查考。
李自成、张献忠其实都算不上没饭吃的,只不过是不好好吃饭而已,所以说他们是说明农民,是万万不确的,因此把不少由游民组成的打砸抢敢死队,把李自成、张献忠说是农民起义领袖实在是当今官方以适己好的牵强附会而已。好勇斗狠加上一些狡狯,使得他们流窜作案,抢劫掠夺,无恶不作。如果你说他们是有针对性地报复朱明王朝的统治,那就是太高看他们了,他们害死的不少人同样是在乡村和土地上辛勤耕耘、尚能有一饭之饱的普通民众而已,而那些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视而不见,历史在他们那里是可以随意选择,为己所用的一块橡皮擦,符合官方口味的便用尽力气去证明,反之则深深遮掩和抛弃在历史的荒郊野外。“摇黄十三家”及李自成、张献忠部长期流窜地四川各地,给四川各地民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是造成明末清初蜀难不容忽视的罪魁祸首。如果从1630年“摇黄十三家”乱蜀开始,到1664年李自成部李来亨败亡,再到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全蜀始平,整个四种在明末清初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空前大灾难。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城市倾毁,寺庙消亡,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元气大伤。从明万历6年(1578年)310万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时(1681年)的9万人,即经过明末清初蜀难后,四川人口只有原来的三十四分之一,从中可窥战乱血腥之一斑;而垦田数字则从万历年间的13万顷到康熙24年的1.7万顷,可见田地荒芜的凄惨景象。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