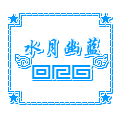六 走向衰落
士族在它的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中世纪西方贵族的权力。他们没能在地方上拥有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不管他们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职,不管他们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庄园,他们终究没有能够掌握对地方的独立行政权。这一点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再高的俸禄,在高的官职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
他们确实可以霸占山川湖泊,但是那些地方只是他们的私人产业。私人的财产权在中国并不特别值钱。西方的封建主可以指着土地说,那是我的!可是中国的士族却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些土地在属于他们的同时,也是属于整个帝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远古的咒符并没有真正消失。西方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有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撑,而在中国,它却是可疑的、变动的、无法预测的。
他们也可以控制众多的依附者。但帝国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这些依附者的管辖权。士族豪强对这些依附者的占有从来都是不合法的。中央政府经常核查人口,和士族争夺这些依附者。俄国的领主曾对农奴说:“我属于沙皇,你们属于我,沙皇可以对我下达命令,但不能对你们下达命令”。这种人身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是封建体制的核心,而在晋代,士族还远远没有能使这样的金字塔完工。
士族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方化,没有能够把地方的行政权、军事权象庄园一样变成世袭所有。他们从地方上得不到的权利,由他们在中央政权中的官职与特权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更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建康,而不是自己的领地,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这些士族在最强盛的时期,也是聚集于建康。他们不能建立真西方那种封建贵族体制。
阅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就连集团势力的消长,也都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往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带有强烈的变动性。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贵族集团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仰或是军人集团,他们彼此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分。在合法与不合法,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士族似乎可以占有土地可以占有人口,但他们似乎也可以被剥夺这些土地人口。中央政府似乎可以可以调动军队,任免将领,但他们似乎也可以被拒绝。一切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说明士族的胜利并非无可置疑。他们仍旧时刻要面对挑战。
更要命的是这些士族应对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阶层本身数量相当有限。当然士大夫多有姬妾,按理说几代人下来,子孙数量应该颇为庞大才对。前些时候,有位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考证说,由于多妻制的缘故,成吉思汗一个人的后代在全球就有千万之巨。这些士族子孙即便没有如此之多,但群策群力,数量亦当不少。当时很不幸,这些子孙里大多必是庶出,他们在当时极受歧视,没有资格顶门立户。可入仕途的嫡子孙数量并不可观。在很小的士族人口基数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度,无疑等于在士族子弟中取消了竞争机制。取消的结果是配置出来王徽之、王复那样的军事白痴、政治弱智。这样的一群纨绔子弟,没有在地方上扎下根,没有牢不可破的实力基础,却投身于变幻复杂的政治冲突之中。一群被优越环境宠坏的子弟,去和皇权与寒族的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如何不难逆测。
但是为什么那些这些接管士族权力的寒族没有成为新的士族?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拆了宫殿,再修一个”。为什么这种循环交替在士族问题上没有出现?这需要用把这段历史放至更大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
汉朝是一个集权化的大帝国,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带有明显贵族化色彩。中国历史在此有过短暂的犹疑,在集权化和贵族化两条道路间难以取舍。但很快,中国又走向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后集权倾向不断加剧,到了明清,就已经到了古代帝国集权的极至。反观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化的封建体制绵延千年之久,给西方历史打上了深深烙印。
产生这种不同结果的最重要原因是帝国官僚管理能力的差异。
在一个分权的、贵族化的国家,出现一个强者并不困难。这个强者也有可能在军事上压倒其他所有的贵族。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强者如何建立一个集权帝国?只在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集权的行政管理,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帝国的权力也才能真正集中起来。而没有官僚组织,他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行政管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军事强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他又该如何管理这个帝国呢?如果他不能向各个地方派出足够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制这些官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托给某个地方贵族。他可以轮换这些贵族,他也可以打击那些对他不忠的贵族,但是他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办法真正控制这些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贵族一定会积累属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对帝国的离心力。
而在中世纪,无论是查理曼大帝还是奥托大帝,他们都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官僚组织。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就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那么,这些帝王又如何用公文来监控那些地方长官呢?他又如何得到各地的统计数据呢?他又如何选拔官吏去充任各个政府组织呢?他做不到,即便他有千军万马他也做不到。可以想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政府机构弄的非常简单,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运转。地方上,如果不出现叛乱暴动之类的大事,就会由地方长官全权处理,而地方长官的行政机构也同样是简单之极。这样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又能实施多少的管理呢?对地方长官又能有多少的控制力呢?地方长官逐渐产生离心力就会象一个自然现象一样不可抗拒。
中国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人员流动程度都大大超出了中世纪的西方。它有能力实施复杂的行政管理,它可以填充、供养精细庞大的的官僚机构。即便在在晋朝,要选拔大量能处理公文的、受过同样意识形态熏陶的的官吏也并非难事。可以说,中国集权的能力已经存在,它不过是没有得到条件来施展而已。而在中世纪的西方,这种条件本身就不存在。为什么奥托大帝没能建立集权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赵匡胤却能建立一个集权的宋帝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资源迥然不同。
中国皇帝们要想释放这种能力,所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贵族。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科举制度。隋唐时代开始推行科举制度,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
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样一个转变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帝王(想想那个流着口水看着别人被剥皮的刘岩),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同样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贵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