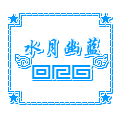四 如何又是待客之道
士族既然按照门第和血统确定官位,就不得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
政治上士族和庶族,判若云泥。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如此。士族子弟往往除了穷嚼蛆以外并无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出身就混个高级干部。如果他不做出一副神头鬼脸的高级派头,又如何能使寒族肃然起敬?如果他不强调出身的等级差别,又如何能在庶族面前理直气壮呢?如果他和寒族通婚,又如何能标榜自己的高贵血统呢?在此逻辑之下,两晋南北朝成了中国阶层隔阂之间最大的时代,虽然没有发展到印度种姓制度的程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匪夷所思。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严格的区分,其严酷程度,较之种族隔离不遑多让。庶族如果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要和士族平等交往,那会遭到严厉打击。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出身于江南豪门。他和中书舍人秋当、周赳是同僚,在一个部门任职。秋当、周赳却不幸是寒族。秋当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作客。周纠本分,说:“恐怕人家不能给咱们好脸子看,不如别去了。” 秋当说:“咱们现在和他是同事了,怕些什么?还怕他不跟客人一起坐坐吗?”俩人就互相壮胆,到张家作客去了。张敷倒确实为他们设了俩个坐位,但怕他们靠脏了自己的墙,就把坐位安排的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俩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召唤左右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 秋当、周赳听了以后,失魂落魄的告辞而去。
寒门、役门出身的人,在士族子弟看来,都属于“小人”。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门。一次他们俩结伴外出,到了中午也没吃上饭。这时候有一个与他们认识的“小人”特意准备了酒席,菜肴非常丰盛。刘惔却拒绝了。王濛的阶级觉悟没有他高,又熬不住饿,就对刘惔说:“聊以充饥嘛。为什么要拒绝呢?” 刘惔大义凛然地说:“孔子曰:唯君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巴解都巴解不上。《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记载到“方正”一章里。但我看不出刘惔方正在哪里,能看得出的只有鼻孔朝天的自骄自大。我们看古画里那些两晋雅士宽袍大袖,神态散雅,但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最龌龊最势利最不可理喻的傲慢。他们贪婪的攫住利益不撒手,然后又用极度虚伪极度做作的姿态,来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霸占了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尚且不足,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分也有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能找出一切可以找出的理由做骄傲的资本。前面已经说过,那些早些渡江的百家士族,就成了贵族中的贵族,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以做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对他人表示蔑视。
唐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说的王、谢就是晋朝士族的两家魁首。但是就算是这俩家,也不是没有级别差异。谢安和谢万曾经路过吴郡,谢万提出去王恬府上拜访。谢安坚决不肯,说:“人家一定会跟你难堪的。”谢万就一个人去了。王恬等谢万刚落座,就忽然起身到后堂去了。谢万看了倒很高兴,觉得王恬一定是去安排家人好好款待他了。过了很久,赫然见到王恬蓬头散发的出来了。原来这家伙跑到后面洗头去了。他也不陪客人坐,自己走到院子里那儿晒头发。神态傲慢,根本没有要搭理谢万的意思。谢万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王恬是王导的儿子,有人说他性格过于傲慢,才会如此。但究其实际,推动他如此行为乖张的,终究是门第的自豪感。王家显赫在谢家之前,如今谢家的风头虽然迎头赶上,但王恬依旧认为自己比谢家人高贵多了,谢家人想在他面前平起平坐,那还早的很呢。他的逻辑是:我的爹(王导)比你的爹牛,那我当然就比你牛。
谢家尚且如此,其他后起之秀待遇往往更加不堪。王家一个子弟王胡之在东山时,偶然贫乏。当地县令陶范是晋初有名的大帅陶侃之子。陶侃曾担任荆州刺史,手中握有重兵,是一个半军阀性质的将军。但是可惜他出身寒族,虽然军兴之际可以侥幸出人头地,但还是被士族瞧不起。一个当兵的!陶范想讨好这位王家人,一出手送了一船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要。王胡之直接回答说:“我要是饿了,到谢家要米也就罢了。那轮的上这这陶的奴才送米!”他有权毫不掩饰地侮辱比他出身低下的任何人,他知道舆论还会表扬他的“方正”,他的“风骨”。这样这样的故事全部搜集起来的话,数量相当惊人。中国的婆罗门们确实用傲慢的火煅铸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等级社会。
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也被这种等级制操纵。士族与寒门役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可为人所容忍。而士族妇女嫁给一个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比起人兽交合,已经相去无几。社会交往中的禁忌在婚姻中受到更大的重视。士庶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就属于“婚宦失类”,后果相当严重。
南朝时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个叫王源的官员把女儿嫁给了富阳的一个富户满璋之的儿子。王源出身名门,父祖也都是有名的士人,但是到了王源这一代,家产却颇为不足。王源就把女儿嫁掉,得了一笔聘金,王源还拿这笔聘金的一部分娶了一个小妾。但是这个满璋之也不是土财主。他自称是魏晋旧族,而且自己也是一个中级官员。新郎官本人也是一个主薄。但是这一下还是惹了祸。大臣沈约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按理说,人家结婚娶媳妇不干他事,但他还是仔细做了调查研究,很警惕地发现了其中的不正常现象。沈约考察了满璋之的家谱,认为里面有伪造成分,满璋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士族,出身不高级。而王源却是高门华胄,和满家联姻,实在是败坏人伦天理。
沈约用优美的骈体文起草了处理意见:“王源自己降低身份门第,其行为玷污了祖宗,侮辱了亲族,性质恶劣至极。这种歪风邪气不煞住的话,败坏人伦的联姻将比比皆是。对于王源的这种可耻行为,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重惩,把他开除出士族队伍。这样一来,那些已经干了同样的勾当的士人,将无比羞愧;那些正在策划干同样勾当的士人,将悬崖勒马。所以,我的处理意见是:把王源就地免职,终身不得再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王源的下场就是这样。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的结果使士族能够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在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来抗议。他们的心态正如杜佑所言:“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有人说这些士族尽得唯美文化之风流雅趣,但我看到分明是一个贪婪的既得利益集团。
但是,这些士族也不能在的成功的巅峰永远驻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利益象沙漏里的沙一样慢慢流出。
罗马将军出征凯旋归来时,罗马城会为他举行巨大的凯旋仪式。将军在人群的欢呼中进入罗马城,这时他的身边总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侍从,在他耳边不断低语:“这一切不过是过往烟云”。
没有人在士族的耳边说起这样的话。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