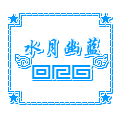二 做官里头还有许多不平处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建立于曹魏时期。它就象老师给学生打分一样,把候选人分为九品,不同品第的人有资格出任不同级别的官员。九品这个想法来源与班固的《古今人物表》。班固在该表里把古今人物从上上到下下做了一个排列:
一、上上圣人类:像伏羲、神农、皇帝、唐尧、周公、孔子等。
二、上中仁人类:女蜗、比干、孟子等。
三、上下智人类:鲍叔牙、百里奚、子贡、范蠡等。
四、中上类:愚公、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等。
五、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吕不韦,荆轲等。
六、中下类:吴起、苏秦、张仪、秦始皇等。
七、下上类:易牙、庞涓等。
八、下中类:夏桀、末喜、秦二世等
九、下下愚类: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等。
对班固这个排列大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比如我就不能理解怎么愚公怎么就排到孙子前面了?但这个无关紧要。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并没有真正按女蜗的水平来考核二品。
这个制度规定,各州都设立大中正,各郡则设立小中正。这些中正官本身都是中央现任官员兼任的,地方官做中正的少之又少。这些官员一般原籍在哪里,就担任哪里的中正官。中正官按照九个品第给候选人打分,将结果申报司徒,最后由中央按照品第高下任官。
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制度会有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由官员给原籍人士打分,他会给一个不认不识的小萝卜头打高分么?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或者世交,一边是小萝卜头,你会把高分打给谁呢?所以结果一定是小萝卜头被淘汰。小萝卜头不服气?说不公平?可什么是公平呢?这个评定又没有标准,完全是自由心证。你说我打的不准?那你说说怎么是准?问谁谁哑巴。
现在参加高考,要高度保密试题,要把考卷上的考生名字都封上,就是怕人作弊。有人说高考制度不合理,应该综合考察素质,应该以人为本,可是在中国这个现实环境里,你怎么去公平的考核综合素质呢?都知道高考制度有问题,但对作弊的恐惧遏制了改革的冲动。反观九品中正制度,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理论上来说,九品中正制考察的就是综合素质,比考试制度要人性化,但人性化的结果是它可以旗帜鲜明的作弊,结果导致了变相的世袭制度。
这样的演变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做中正的时候不选拔士族大姓的后人,那么,等你下台了,人家又凭什么选你的儿子?给你儿子评个末入流,他就只能在避马瘟的官职上消磨一生了。所以,你当然会选拔大姓名门的后人,广种薄收,以后也好有个结果。别人上台做了中正,自然也会依法炮制。这种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做法,就有了一个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天长日久,按照门第品评登记就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法”,不这么干的人就似乎严重违反了天理人伦,在官场上就混不下去。
这样的制度刚刚运转的时候,还会打出招牌说“要考核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连这个幌子都没了,直接按照门第打分,最终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做法最终突破了潜规则的范畴,成为正式的人事制度。从皇帝到寒族,都承认它的合法性,没人认为这是舞弊。舞弊舞到不是弊,就是舞弊舞到了化境。一个贵族化的寡头统治,也就在这种化境中脱胎而出。
中正九品制说是九品,其实是八品。因为第一品被认为实在是太高级了,只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配得上。所以第一品被虚位以待,品评从第二品起。而且也只有第二品值钱,被称为“灼然”,“上品”,被士族子弟垄断。二品以下直到九品的都是“下品”,“寒素”。门第制度成型以后,士族就被称为“高门”,高门里面出的自然都是高人。庶族被称为“役门”,意思是他们都是些只配给高人服役的下等人。
中正九品考核的据说是“人品”,当官讲究的是“官品”,比如太守是五品官,县令是六品或者七品官。“人品”和“官品”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人品”二品的士人,不到二十岁就可以出来当官,而且这些人仕途顺畅,都能干到五品以上的官员。而“人品”二品以下的,一般三十左右才能出来当官。担任官职也都基本是六品以下。五品官成了一个鸿沟,把士族和寒族划分开来。寒族出身的县令,哪怕象焦裕禄一样在职位上干的吐血,也是没多大指望给提拔成太守的。
出身不一样的官员,在仕途上处境大不一样。明清时际,实行科举制度,考出来的官叫进士官,考不中花钱捐的官叫“科贡官”。这两种官,待遇大大不一样,科贡官见了进士官处处低一头。《警世通言》里一个老秀才鲜于同就誓死不做科贡官,一定要考。他的理由是:“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撤漫做去,投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未,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砧,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勾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抖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不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
晋朝役门出身的官员就有科贡官的苦恼,“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按照《通典》作者杜佑的说法:“衣冠士族和寒门百姓之间好有一比,就像大树和杂草一样。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就好比砍掉了一根杂草罢了。大家看了庶族被怨杀,就算不喜笑颜开,也不会为他们悲叹的。这样不杀士族只杀庶族,不是很好么?”捧着卵子过桥的人,看来也并不安全,很可能成为替大树顶岗的杂草,被领导诛杀。
不过“役门”并不是最糟糕的。能被中正官品一品的人还算是有福气的。更多的平头百姓是没资格被“品”的,这些杂草就被称为“吏门”。他们如果想报效朝廷,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小吏。那时的小吏地位和被“品”人士相比,也是隔如霄壤。官员们上厕所,还可以指派小吏在茅厕里给他们举蜡烛。现在即使比较丧心病狂的领导,也很难提出让手下在茅房里给他们打手电筒的要求。这当然说明时代进步了。
高门、役门、吏门就构成了吏民的三个层次。作为高门的士族,垄断了高级官职,控制了政治局面。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