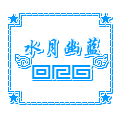一
1955年5月发生的胡风(1902—1985)事件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历史尘埃早已落定的今天,这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参与者和许多受难者大多已远离我们而去,而遭殃及的健在者也都是耄耋老翁了。但是,这个事件留下哪些特别内涵值得我们长久记忆呢?对这个悲剧本身灾难性的规模、影响、意义与走向及其前因后果,我们能作出今天所能认识到的回答吗?我以为,我们如果把胡风事件放到涉及毛泽东(1893—1976)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
胡风事件所起的历史作用,较之前所发生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乃至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批判,从历史链条的环节上看,都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以后历次实际政治较量的操作中,唯有胡风事件一直被作为开展政治斗争的“惊堂木”的警告符号,而贯穿于中国政治风暴的全过程,直至这场风暴完全平息为止。20世纪80年代为胡风冤案的平反,竟历经三次(1980年、1986年、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这也是全国所有冤、假、错案的平反中的唯一。综观全局,胡风事件的独特意义,由此也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毛泽东晚年曾高度概括自己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革”打倒自己身边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毛的原话大意是 :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刘的不满,毛在1950年3月意欲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受刘的搁置时就初现端倪了。虽然毛与刘这次政治较量声色未露,其内心郁积的愤懑,迟至1967年4月1日,才通过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的发表大白于天下,但事情的发生,则早于胡风事件五年之久。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毛在这里把无职无权的、当时连工作岗位都尚未确定的一介文人胡风,列于一连串曾经显赫过的人物之首,绝非偶然。原因何在?在于毛潜意识的未来的棋盘上胡风事件还要派上更大的用处。胡风事件搞定后,无论对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还是开展所谓“对敌斗争”,其实际的功利主义价值,都不是这些显赫者的效应可以比拟的。
二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建政之初,不断开展斗争,继续革命巩固政权,几乎是一切工作的全部目的;而斗争锋芒在扫除了正面之敌对势力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之后,则越来越转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寻找与搜索。毛亲自发动的运动有: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继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再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又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两个由“点”到“面”的回合中,基本上止于思想斗争,没有涉及到对具体当事人如编剧孙瑜、主演赵丹、红学家俞平伯等的人身斗争,更不必说对鞭长莫及、远在美国的胡适了。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前导,都还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警示作用;而这一具备特殊政治指向的斗争工具,还有待于在不断展开的动的动向中去寻觅、挖掘或随机捕捉。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作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一直到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胡风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胡风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认为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产主义者的为人道德约束自己”(《胡风致熊子民》,《胡风全集》第9卷第599页),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者,感觉没有什么好检讨好改造并拒绝检讨。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也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见笑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2002年第8期《文史精华》)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牴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毛泽东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日,毛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胡风曾三次见到毛:一次是9月4日,由冯雪峰陪同在曾家岩50号欢迎毛的舞会上,仅握手略略交谈几句走了过场;一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500余人参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是10月11日,在欢送毛回延安的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早在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上发表过《毛泽东论鲁迅》。这是毛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的首次发表(同天,胡在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被推为大会主席)。这是两人在两地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文字之交,又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本可引为谈资的;但在晤见时,经过抗战八年的烽火,似乎都淡忘了,连一句寒暄的客套话都没有留下。这三次不冷不热的见面相识,虽然从胡的方面说,显示其在高层社交场合多少有点腼腆、矜持的书生本色,但从毛的方面,与其说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说是有意的冷淡。因为这次会晤之前,毛对胡产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
但,毛这次与胡的会面,对其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终于把久闻其名的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露锋芒的、在鲁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为焦点人物出现的、与自己一同列名于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在延安与周扬以及徐懋庸等从上海来的文化人的交谈时屡屡提及的、只是见于书面文字或耳闻的胡风,和眼前这位零距离接触的、与自己身躯一般高大的、显得矜持而书生气十足的胡风联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内心对胡却是“十分重视”的。
1945年10月11日,毛与蒋签订《双十协定》后从重庆抵达延安,即指派与他同机往返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第二天再飞回重庆,专程调查重庆左翼文化界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胡风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在机场看见了胡,触动了毛的政治“灵感”也未可知。这个安排,自非寻常。胡乔木飞回重庆后,约见胡风两次,在文艺理论上硬是谈不拢。后胡乔木又通过胡风约见舒芜,就舒在年初由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论主观》、《论中庸》两文的哲学问题,在11月8日、9日,激烈地辩论了两个半天。胡乔木概括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参见《百年潮》2004年第11期第41页)胡风始终在场,未置一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刚刚召开过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已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延安所及的范围内,包括重庆的左翼文化界,对此已是一片称颂赞扬之声,胡风的态度只能被认为是冥顽不化了。
胡在文艺理论上,与毛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与冲突,在1945年后,越来越趋于明朗与尖锐。源于40年代初,由于胡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并因逐步形成由自己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呼应,胡愈发不屈不挠。用鲁迅生前曾经批评胡“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答徐懋庸》)的话说,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1940年10月,胡风在重庆发表长达5万余言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对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了像别林斯基似的“鸟瞰”:对延安与重庆两地的论争参与者,如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张光年)、叶以群、胡绳、罗荪、巴人、周扬、何其芳、黄芝冈、田仲济、陈伯达、艾思奇、张庚、向林冰等,一一点名批评。用周扬后来的话说,胡把左翼作家批评尽了,是反对民族形式的。(胡风同仁在40年代办的好几个刊物,都承传了胡这个毫无忌讳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的作风,被得罪的作家不在少数,这里不一一列举。但这却也为后来的胡风事件的一哄而起,上下互动,在客观上预设了“干燥的柴火”。)胡的基本观点,认为民族形式不是民间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的新文艺形式才是民族形式,因为它是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是不能也不该倒退到复古主义的民族即民间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个理论虽然可从列宁的每个民族有两种文化的思想找到根据,但中共高层的观点是“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中共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当时的中共,要宣传、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千百万群众投身革命与战争,亟待确立以民间形式为主的民族形式以教育之,这就不能不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40年代初毛关于整风运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政治学习文件传到重庆左翼文化界,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质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而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等则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颇有点“离经叛道”的观点。胡风又著文引申为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教条主义,与延安反对王明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成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
《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董必武当即按照组织原则从事,迅速作出纠正,乔、陈当然也只得接受党内批评。乔、陈虽与胡交往不疏,或许碍于纪律似并未将内情告之,而胡仍浑然不觉;或许胡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继续我行我素。1944年7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还有后来的舒芜的《论中庸》,引起了毛对胡的严重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胡虽然在30年代初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但却只心甘情愿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还不适应时至40年代该以毛泽东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公式为本体的事实,并认为在政治上与中共为“同路人”,在文艺上自己可以有独立见解,这也是胡风所服膺的鲁迅的观点;而在毛看来,一节问题都从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理论、学术、文学等可以游离于政治问题之外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胡只是“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尚不甘心服膺于自己理论的、时不时还要中共(通过周恩来)提供办刊物经费或道义支持的一介文人而已。不屑还来不及,热情更谈不上了。
这次毛泽东与胡风见面后,毛很快从军事上、政治上,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与国民党的最后决战。处于日理万机状态的毛,不可能对胡的文学活动多所关注,但反映到中枢的几件事,则很可能进入了毛的视野之中:
(一)1948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的对立。这显然是一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举措,当然也是借以进行政策调整的举措之一。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
(二)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出席了大会。7月3日,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有句“只准自己批批任何人,不准任何人批评自己的歪风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应该为我们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不取”。7月4日,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其中有“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对胡不点名的批评。胡是茅盾报告起草人之一,因有异议而未参加,这符合胡的性格。茅在报告后的《附言》中注明“胡风先生坚辞”,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因故”或“因事”之类的托词,其不合作的态度显得很触目。7月6日,毛“突然”亲临大会,发表简短的“欢迎你们”的讲话即退场而去。郭、茅的报告,恐非毛过目不可,而胡的“表现”毛当了然。
(三)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12月周恩来约见胡,1952年4月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胡30年代的左联盟友,后被胡案株连)陪同下访见胡,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
(四)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


 水月幽蓝
水月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