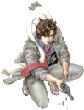军乐起源之争
关于军乐的起源人说纷云。其一,是苏联军事大百科全书中的记载:军乐出现于上古时代,在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埃及、严述、巴比仑、巴勒斯坦、中国、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有军乐。而许多欧洲音乐家们则认为,欧洲的军乐来源于乐方的土耳其。理由是:当年的腓特烈(也译弗里德里希)二世统帅的普鲁士兵团于1740年在其指挥的军队中建立了“土耳其式”的军乐队。这种军乐队使用的东器是由小横笛、高音直萧(一种有哨子的萧)和各色各样的喇叭、系在腰上的大鼓、镲、三角铁、锣、铃架(挂有许多小铃的架子)所组成。军乐队随军行进,并且用嘈杂的喧闹声和强烈的节奏来恐赫敌人。
比较起以上两种说法,后者有失客观的太度。因为它是以装配军中的完美程度为前提的。就算从完备程度上看也无非和我国汉代时的“鼓吹”军乐相仿,但时间上比汉代“鼓吹”军乐晚了2000多年。甚至比戚继光威风凛凛的中军旗鼓阵还要晚了近200年。
我们来看一下戚继光中军旗的阵营:
清道旗 清道旗
有箍快枪 有箍快枪 有箍快枪 箍快枪
鼓 鼓 鼓 鼓
孛罗 号头 号头 孛罗
金 唢呐 唢呐 金
金鼓 金鼓 金鼓 金鼓
点子鼓 铜鼓 铜鼓 点子鼓
笛 笛 笛 笛
笙 小鼓 云鼓 钹鼓
号头 孛罗 孛罗 号头
扁鼓 扁鼓 扁鼓 扁鼓
炮手 唢呐 唢呐 炮手
看了这个门阵列,或许人们会认为是一种节庆时的秧歌队,要么就是梨圆中杂耍班子。然而,它却是明代将领,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本营直属军乐队,乐手有五六十人之多,乐队的配备程度与土耳其式的军乐队只有乐器上的区别。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比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说法:最原始的军乐是被用作战场上的指挥军队和规定的部队日常生活制度的信号,后来开始被用来鼓舞军队的士气。由此可见:在战场上,军乐以鼓壮军威为第一职能,它以观赏性和音乐艺术性为第二职能。根据这一理论,早先军中出现的号角和战鼓都是起鼓壮军威的作用,更何况它们同样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那么,军乐的起源便应以鼓号在军中出现的年代而确定。这样一来,军乐起源的年代便被大大提前了。同样也远远超越了古希腊的年代。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说法。似乎每个国家和民族具备大量的史料证据说明军乐起泊于他们的国家,最早出现在他们的民族之中。
军乐起源之争还在继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战争就有军队,有军队,军乐也就随之产生。
中国近代军乐的创始人李映庚
李映庚(1845-1916),曾历任永平、正定、大名、天津、保定、邢州等七地知府。民国建立,映庚升任肃政史。职责是监察各部员司的违法乱纪行为。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冒天下之在不韪,欲复辟称帝。映庚以言官身份上书谏止,因不被采纳愤然辞官。他回到沭阳后,由于德高望重,被公推为沭阳县农会会长,制“整治沭河方案”,未及实施,即于1916年11月15日逝世。
李映庚生前,除在政界是有一定影响外,在新的军乐方面亦颇有建树。李映庚的音乐功底是在少年时期打下的。清朝末期,苏北地区昆曲颇为流行。李映庚青年时就喜好昆乐,他和其弟李燕卿经常相聚一堂,弹唱切磋技艺。他们精通音律,步入仕途以后,从政之余,仍以吟唱昆曲为乐。他的昆曲唱得很好,在北方昆曲界颇有名气,著名京昆名伶陈德霖和王瑶卿早年都曾随他学过昆曲。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因“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屡受外国列强的武力胁迫,意欲扩充军备以自强,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于天津东南70里处的小站主持训练新军――武卫右军。李映庚当时任天津知府,因他通晓音律,袁便请他主持,从西欧买回一批钢管不器,仿德国陆军的建制,为新军创建了一支军乐队,并在天津成立“军乐传习所”,李映庚兼任所长,新授军乐。起初,他指导新军乐队用铜管乐演奏了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气势雄壮,震撼人心,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并奖给他一些银两。为鼓励乐队队员刻苦训练,他当即把全部银两分给队员,自己分文不留。此举遭到新军雇用的西洋乐队忌恨,遂集体离去,企图胁迫李映庚屈服。李映庚决心以自己培训的中国乐队代替西洋乐队,以反帝爱国军乐代替西洋军乐。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李映庚将部分昆曲曲牌化简,运用昆曲的“同场”唱法,按拍形成进行曲的节奏。历时三个月,创作出军歌10余阕,这是李映庚的一大创举。昆腔自形成至此,已成500余年,不外乎在歌楼舞榭,供人茶余饭后欢娱而已。而此时,李映庚将它的曲牌运用到军乐中去,以其民族特有旋律让士兵吟唱,借以激劢斗志,振奋军威,为反抗帝国列强的侵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映庚在正定知府任上,深恐旧稿因年久而散失,于是收拾历年旧稿加以整理,分为四卷。卷一为表,计有《中外字谱表》、《中外律吕表》、《中外律吕旋宫表》;卷二为配词乐谱,乐谱全部用我国传统的“工尺谱”记写,计有《神武颂》、《升旗颂》、《望阙吟》、《飨宾歌》、《飨士歌》、《军宴歌》、《军祷歌》等7首共20阕;卷三为军中散曲,也是配词乐谱,计有《男儿汉歌》、《宝刀歌》、《铁血歌》、《从军行》等10首共43阕;卷四有谱无词,为军中礼乐,计有《军中迎送之乐》、《军中行礼之乐》、《军中走队之乐》、《军中定席之乐》、《军与军相遇致敬之乐》等5首。卷二、卷三的曲谱下均注明用中乐伴奏或用西洋乐伴奏,卷四的“军中礼乐”则注明全部用西洋乐器演奏。过去所用的昆腔曲牌,在李映庚的手中,一跃而变为激励将士斗志奋而保家卫的精神武器。至清宣统元年(1909)春,上述四卷书题名《军乐稿》,石印出版。《军乐稿》成为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一部军乐专著,而李映庚,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近现代军乐的创始人。
袁世凯创始中国现代军乐
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练兵,聘来许多德藉顾问,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高斯达的,向袁世凯建议把军队里所有的长号筒换成西洋喇叭,编制号谱,同时组织一个军乐队,招收聪慧青年数十人,加以训练。袁世凯同意了高斯达的建议,于是,中国的现代军乐有了一个简单的开端。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袁世凯奉了慈禧太后的命令,在天津开办了一个类似学校的军乐训练机关,这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八十人,另有一个旗人队,约五十人。他们毕业以后,就被分发到当时的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服务。每逢新年,这六个单位的军乐队还要到天津集合,参加考试,连接举行了三次。
袁世凯为军队的军队人数做了明确的规定。步兵营(五营)用军乐兵一百二十人,炮兵营(一营)用二十四人,骑兵营(一营)用十二人,工兵营(半营)用六人,合计一百六十人。
关于军乐队员的“饷章”,袁世凯也做了规定,每名军乐兵每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骑兵营则每名每月支“食乾银十一两”,多于工兵营军乐兵工食银若干两。
每支军乐队配备管乐器十四只,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
对于军乐兵的训练,袁世凯开始就有“按号乐总教习洋员高斯达禀呈的乐规训练”,并告戒所有的军乐兵必须遵办母违。
另外,军乐兵在出操,换班场合应注意的事项,袁世凯也做过若干规定。例如:“换班时,新班之官宜带领队伍击鼓吹号整队前进”“统帅到达某营,护军队应列队双手举枪,军乐队鼓号迎送…”,“骑兵军乐队练习,如是一字操步法时,号兵与二行的排头要有四步的距离。一开操,号兵即可散开…”。“行军时,领官带护勇持队旗及鼓号兵在队伍的最前列…”。“路过村庄集镇或练完操进入军营时,军乐队必须击鼓吹号,各兵托抢按步法前进。”等等。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军乐的发展,的确有着袁世凯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军乐延续下来的民族“鼓吹”的历史。
一九零零年九月六日,德国莱比锡发行的《图事杂志》,有一篇没有作者的文章,叫做《北京使馆之围》,它报导了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始末,文中并介绍和当时有关的几个德国人的生平及中国北洋军的实力及武器,配合这篇文章,有几位欧美人的照片,五幅北京城风景照片,二幅中国炮兵和他们的洋教练及一幅中国西式军乐队的照片。在照片下方有一幅题为“中国军乐队,由一欧人指导”。
图中有一个站得笔挺的洋军人,是不是高斯达已无法考证,他的右手持指挥棒,围绕他而站的是十六保中国军乐兵,乐器为短号七支,伸缩号二支,不同音域的巴雷同号三支,士巴号一支,黑里空号一支,小鼓一个,大鼓兼钹一人,另外还有轻便乐谱架十一架,架子上都放有乐谱,军乐兵都穿着清末的军棉袄……。
因为它是清末少数中国现代军乐队照片之一,它显示了当时所用的乐器,证实了欧洲教练的存在。并且告诉人们,这支军乐队已不只是吹作息信号的号手,而是可以视谱,听从指挥吹奏分部(大小不同的乐器)的西式乐曲的新型军乐队。
袁世凯的军乐除了在慈禧太后巡幸奉天时为其演奏外,还常常被调入紫禁城演奏,普在清廷担任过御前女官的裕容岭在《清宫琐记》中谈到:“有一天,李莲英对我母亲说‘五姑娘会舞蹈,让她跳给老佛爷看看’。我母亲便问我:‘你对中国的古代舞蹈研究得怎么样了?’我说:‘我倒是练了好个了,一个荷花仙子舞,一个扇子舞,一个如意舞,还有几个都练熟了。外国的跳舞服装,我倒是从法国带了几件,可是没有音乐’。李莲英说,“外国音乐不成问题,袁世凯有西洋乐队,可以把他们从天津传来”。李莲英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慈禧便传旨把袁世凯的军乐队叫到北京来。
“五月初的那天,我在乐寿堂的院子里表演跳舞,地上铺了一张大红地毯,一连是袁世凯的西乐,一边是太监们组成的中乐。”
后来,袁士凯称帝,更是让军乐在中南海不停地奏响,末代皇帝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一文中写道:紫金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处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理象叫做“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 “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军乐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想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不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煽着扇子。”
傅义的回忆录使我们看到了袁世凯军乐的一个侧面,。后来,傅义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英国兵营的军乐队进宫演奏之后,他就列觉得中国的丝竹弦不堪入耳!……。


 apple
ap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