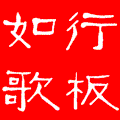七、德沃夏克
Antonin Dvorák
安东宁·德沃夏克
1841-1904
捷克作曲家。1841年9月8日生于布拉格。自幼学习小提琴,1857年在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先后在布拉格的一个乐队和布拉格临时剧院担任乐手。1871年辞去剧院乐队工作,以教课为生,此外兼任教堂风琴师。1873年他的作品《白山的子孙》首演成功。1875年受到勃拉姆斯赏识,此后得到勃拉姆斯热情的关心。1878年在布拉格举行他的作品演奏会。1888年结识柴可夫斯基。90年代多次在欧美旅行演出。1892年就任纽约国立音乐学院院长。1894年回国,在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课。1901年5月1日在布拉格逝世。
e小调第九号交响曲《自新大陆》——许多大艺术家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自虐倾向。看看贝多芬、布拉姆斯、舒曼、柴科夫斯基、梵高、尼采。或许,经过情感的压抑,工作上的自律,艺术本身的最美质地才会被挤压出来?德沃夏克却不是这么回事。身为屠夫之子,长得又像拳师犬,德沃夏克开朗、乐观、温文、随缘;他喜欢鸽子咕咕叫的声音、喜欢“看火车头移动”,偶尔还会喝个烂醉。
一八九二年,德沃夏克接受了美国纽约国家音乐院的邀请,到新大陆做起了旅行学者。三年下来,乡愁小小,谱成了这首质朴、诚恳、优美兼粗犷的《自新大陆》交响曲。不过不要被标题误导了!原文是"From the New World",而非"The New World"——它并不是描写美国的写景音乐,而是一封来自异乡的浓郁家书!
八、马勒
Gustav Mahler
古斯塔夫·马勒
1860-1911
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1860年7月7日出生于波西米亚出生于的卡里什特,父亲是一个小酒厂老板。马勒很早就表现出音乐天才,6岁开始学习钢琴,15岁进维也纳进音乐学院,随爱泼斯坦(Juilius Epstein)学习钢琴,后改学作曲及指挥。1880年在奥地利北部的一个小剧院担任指挥。1885年在莱比锡指挥门德尔松的清唱剧《圣·保罗》获得巨大成功。1888年受聘为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指挥。在此期间指挥莫扎特和瓦格纳的歌剧,深获勃拉姆斯的赞赏。1891年担任汉堡歌剧院乐团指挥,后又在莱比锡担任著名指挥家尼基施(Arthur Nikisch)的助理指挥。1897-1907年受聘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这十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对乐团进行了大力改革,使维也纳歌剧院成为世界一流的剧院,同时也确立了他作为当代伟大指挥家的地位。但由于他的不肯妥协的个性,遭到了许多敌对势力的攻击,不得不于1907年离开歌剧院,旅居美国。在美国纽约的三年中,他担任过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和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但始终处于动荡之中。1911年因病返回欧洲治疗,1911年5月18日逝于维也纳。
在指挥方面,马勒是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
马勒在学校期间即开始创作,1899年发表了《第一交响曲》,此后共写了10部交响曲、4部乐队伴奏的声乐套曲、一部清唱剧及5首歌曲。他是交响乐发展史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交响乐作品发展了维也纳古典交响乐的传统,同时多取材于民间音乐,主题起伏跌宕,气势磅礴,结构宏伟,规模庞大,其中《第八交响曲》有“千人交响曲”之称,多数作品都加入了人声合唱。他的《大地之歌》中,还使用了一组联篇的中国诗歌(cycle of Chinese poems)。此外一般认为,他的作品受他的朋友、哲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很深,有着浓重的悲观情绪。
第二号交响曲《复活》——马勒,唉!该怎么说这个人呢?一个拥有无与伦比的意志力的指挥家,一个卯起劲来写作时六亲不认的痴狂作曲家,一个饱览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堕落、糜烂和虚矫的旁观者,一个经历许多至亲的人死亡的悲伤的人,一个兼矛盾复杂的难以复加的忧心灵魂。马勒“第二”的威力我可以作证。一九九九年八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师兄在萨尔兹堡听了拉图(Simon Rattle)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这首曲子。据说这一天也是他的艺术良知重生的日子。音乐进行到中乐章时,他被音乐重重地击打、质询;他知道自己努力得不够,投入得不够,丢掉的东西太少,渴望的力道太弱。他说当时深切的感受到平日里老师一再强调的艺术是没得妥协的,而平庸(mediocricy)正是艺术的头号杀手!当时他无法控制地嚎淘大哭了起来,带着痛苦、自责、羞愧。更多的却是被“敲醒”的喜乐和重生的兴奋。末了,隔座的德国老先生紧握着他的手,同样眼眶红肿的说:“我知道!我知道!”事后我的那位师兄对我说:“瞧!音乐无国界,是你、我、他共同的语言。”
九、西贝柳斯
Jean Sibelius
让·西贝柳斯
1865-1957
芬兰作曲家。1865年12月8日出生在芬兰中南部一个军队卫戍防地小镇海门林纳(Hämeenlinna),父亲是驻军外科医生。西贝柳斯9岁起学习钢琴,14岁学小提琴,并自学作曲,后参加业余室内乐团,他曾希望成为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而非作曲家。1885年进入赫尔辛基大学法律系,不久转入音乐学院,随韦格利乌斯(Martin Wegelius)学习。1889年毕业。这年他的弦乐四重奏公演,得到好评。1889年赴柏林,随贝克尔(Albert Becker)继续学习作曲,次年至维也纳,师从戈德马克(Carl Goldmark)深造。1891年回到赫尔辛基,写下了和声交响曲《库勒沃》,1892年首演,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致力于创作。1893年执教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1897年,芬兰政府肯定了他的成就,开始为他提供津贴,使他能够专心作曲。1900年,他的《芬兰颂》首演,大大激起了芬兰人的爱国思想。1904年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受到来自国外的许多邀请,到各地巡回演出。同年定居赫尔辛基近郊耶尔文佩的艾诺拉别墅(Villa Ainola, Järvenpää)。1914年访问美国,接受耶鲁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回国后过着隐居生活,但仍从事创作。1929年起停止创作。1957年9月20日逝世于耶尔文佩。
西贝柳斯一生创作了100多部作品。他的曲作,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因而获得了芬兰和世界的公认,被认为是19世纪民族派浪漫主义音乐最后的代表人物,为芬兰音乐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
1950年起在赫尔辛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国际音乐联欢节——西贝柳斯音乐周。1965年,中央乐团曾在北京举办西贝柳斯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
D大调第二号交响曲——北欧人几乎都有一种罕见的优美特质:安静、内在沉稳、理性而开朗。是否和他们所处的严酷自然环境有关系我不知道,但从社会主义可以在北欧诸国行得通甚且繁荣安定,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北欧民族个体的私心是比较少的。西贝柳斯做为芬兰音乐的代表,作品永远忠实地呈现他心爱的土地的风貌和他心爱的同胞的内在质地。第二号交响曲是西贝柳斯的作品中除了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外,比较容易切入的。空旷、冷冽、严峻固然是基本的氛围,偶尔渗透进来的温暖、赤诚、热情,以及终乐章的磅礡,保证令您招架不住!
十、肖斯塔科维奇
Dmitri Dmitrievich Shostakovich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1906-1975
苏联作曲家、钢琴家。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9岁开始跟母亲学习钢琴,1916-1918年在格拉泽尔音乐学校学习。1919年进入彼得格勒音乐院,曾得到格拉祖诺夫的鼓励和帮助,从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从施滕贝格学作曲。1926年其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上演,获得巨大的声誉。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探求以音乐为祖国服务。因此,其后几年的作品,或者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如献给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交响曲(1927)和第三交响曲《五一劳动节》(1930),或者具有辛辣的讽刺性,如歌剧《鼻子》(1927-1928)和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30)。但是,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和芭蕾《明亮的小溪》却遭到批评,1936年《真理报》刊文斥责他“否定了歌剧的原则”、是“彻头彻尾的非政治倾向的虚构”。他的第四交响曲也在排练时被撤下。
但肖斯塔科维奇并没有消沉。1937年,他发表了第五交响曲来挽回影响,副标题为“一个苏维埃艺术家对正确批评所作创造性的回答”。然而此后他回避舞台多年。1937-1941年,他在列宁格勒音乐院教作曲。1941年列宁格勒遭受德军围困时,他当过消防队员。在这种生活经验中产生出他的第七交响曲(即《列宁格勒》交响曲),描写和平、斗争与胜利。1943年他定居莫斯科,担任莫斯科音乐院作曲教授。
1948年2月11日,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以及其他四名作曲家遭到了苏共中央的指责。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又一次地被宣布为“左倾的”和“资产阶级堕落”的表现,并被解除莫斯科音乐院教授的职务。肖斯塔科维奇做了“改正错误”的保证。结果,他创作了一系列严格遵循党的方针的作品,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此他在1950年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但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都没有写出有巨大影响的作品。
1953年,他的第十交响曲问世,这首交响曲开创他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阶段。此后他创作了第十一到第十五交响曲,第六到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两首大提琴协奏曲,(根据叶夫图申科之词而作的)《拉辛之死》,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和中提琴奏鸣曲、还有《米开朗基罗待组曲》等。
1957年,苏共中央书记德·谢皮洛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联作曲家代表大会上,就1948年党中央有关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决定做了平反,肖斯塔科维奇和哈恰图良被选为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
1960年,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年9月24日,他被授予苏联的两种最高奖赏:“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列宁勋章”。
1969年他得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此后健康情况一直不佳。1975年逝世于莫斯科。
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都标志着种种趋向极端的感情——悲剧性的紧张、怪诞,非同寻常的机智、幽默,冷闭式的模仿和粗暴无情的讥讽。患病以后,他的音乐似乎笼罩上死亡的阴影,而晚年的一些伟大作品中,总有一种非凡而使人惊惶的力量和紧张。此外,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阴暗和苦涩,反映出与外部事件和环境有关联的深刻的精神痛苦,而正是这种内心的压力,使他创作出一系列的杰作。
肖斯塔科维奇大部分创作都以新的内容丰富了传统的古典形式。他对马勒有深刻理解,遵循马勒开创的先例,总是把平庸和崇高并列在一起。他还研究过当时的西方先锋派(贝尔格、欣德米特、克热内克),并在他的歌剧《麦克白夫人》中留下影响。
d小调第五号交响曲《革命》与其说这首交响曲是一首极权政治底下的抗暴史诗,不如说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在铺天盖地的谣言中,消耗内在的自由生气所写出来的一部狂人日记。当中,我们尝到了血、喝足了泪听到震耳欲聋的控告和超现实的嘲讽,更感受到锥心的疼痛和几近无助的吶喊,即使如此,稍纵即逝的乐观和希望,却不吝为我们开启一扇可以窥见那奶与蜜质地的窗户。反观我们今日所处的状况,“自由”早已成了天赋人权,许多的事情垂手可得。


 行板如歌
行板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