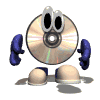激动社区 爱乐之城 · 一曲倾心外语单曲 [2006-5-16]晴朗的一天——选自蝴蝶夫人
- · 谢谢分享感谢了{8/12} 谢谢分享感谢了{8/12} ( skoda01 发表于 2016/10/26 16:04:00)
- · [quote][center][color=#7E7400][b] [mjimg]http://w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16 15:06:00)
- · 一丝不苟的荐析,使古典艺术逐渐融入大众百姓欣赏之列.谢谢.....{76} {65} {109} ( qiaokan 发表于 2006/5/16 16:51:00)
- · 经典啊{63} {63} {63} ( 梦回鼓山 发表于 2006/5/16 17:33:00)
- · 这是FRENI的演唱,不是黄英的! ( corelli 发表于 2006/5/16 18:42:00)
- · -------- cadenza 朋友写的趣闻: “据可靠消息称:Freni从来没在舞台上完整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16 18:47:00)
- · [quote][i]最初由 corelli 发表[/i] [b]这是FRENI的演唱,不是黄英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16 18:50:00)
- · {76} {76} 支持一下赵大哥 ( 水晶梦 发表于 2006/5/16 19:12:00)
- · 谢谢楼主带给我们的享受~~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幻想的话,我是想借这里一席之地,请教诸位: 谁知 ( yddf 发表于 2006/5/21 23:13:00)
- · 我在网上查到这么一则小小的、然而颇振奋人心的消息: *********************** ( yddf 发表于 2006/5/21 23:35:00)
- · 二战以后欧美歌剧都改用原文演唱了,中国歌剧教育还在传播普及阶段,用中文演唱有一定作用,但赶上国际音乐 ( corelli 发表于 2006/5/22 0:18:00)
- · [quote][i]最初由 corelli 发表[/i] [b]二战以后欧美歌剧都改用原文演唱 ( yddf 发表于 2006/5/24 12:15:00)
- · 类似yddf这样的回帖,目前可以说很少,是应该更多一些,那样才是论坛!这才能有沟通与交流,yddf谢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24 13:19:00)
- · [quote][i]最初由 yddf 发表[/i] [b]……一个不懂意大利文的人,他是无论如 ( yddf 发表于 2006/5/24 23:36:00)
- · [quote][i]最初由 行板如歌 发表[/i] [b] ……《啊,明朗的一天》是这部作 ( yddf 发表于 2006/5/25 9:08:00)
- · [mjimg]up_file/2006/5/26/lion_200652618020857197 ( yddf 发表于 2006/5/26 18:01:00)
- · 感谢yddf !{72} {65} {63}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26 19:51:00)
- · 洋洋万言,足见yddf网友对这首歌剧唱段的的衷爱。外国歌剧作品精彩的译配的确会为音乐增色许多 ( corelli 发表于 2006/5/27 20:24:00)
- · 嗯!这帖内容多一点!没有打情骂俏,没有简单的顶贴!不错! ( 舒伯莱姆 发表于 2006/5/28 18:02:00)
- · 回复帖作为主题帖一部分应该是完整的一个组合,我认为此帖可以加精,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帖子像这样的帖子一样 ( 行板如歌 发表于 2006/5/29 0:07:00)
- · 美不胜收 ( Injoy01 发表于 2006/5/30 16:44:00)
- · 谢谢分享{76} {76} ( suiliang 发表于 2006/10/11 20:15:00)
- · 很喜欢,谢谢 ( myy1972 发表于 2008/1/18 15:17:00)
- · 真的太感谢楼主了,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歌声!!!FRENI我的最爱! (游客 发表于 2008/8/11 11:16:00)
- · {8/13} ( kulouzi 发表于 2008/8/11 14:46:00)
- · {8/14} ( mrj8964 发表于 2008/8/16 16:11:00)
- · {8/57} ( mrj8964 发表于 2008/8/16 16:24:00)
- · 至美。{8/13} ( laoliu2260 发表于 2008/8/23 17:41:00)
- · qidai ( aorsenwxjd 发表于 2008/10/7 8:18:00)
- · xihuan madam butterfly ( ademan 发表于 2008/10/9 3:16:00)
- · ......0 . (游客 发表于 2008/10/19 12:00:00)
- · 好好! ( cat2_bibi 发表于 2008/10/19 12:03:00)
- · 谢谢分享 ( MPCD2008 发表于 2008/10/22 2:02:00)
- · Thanks a lots ( ano0408 发表于 2008/10/28 17:47:00)
- · 謝謝分享 ( yaoqiusheng 发表于 2008/11/2 8:07:00)
- · 谢谢分享! ( zakuz 发表于 2008/11/20 16:32:00)
- · 非常感谢! ( laehsueh 发表于 2009/7/6 6:48:00)
- · 抒情的歌唱。{8/57} {8/54} ( lwz4918 发表于 2010/2/4 21:23:00)
- · 谢谢分享这美妙的音乐。 ( ren19562 发表于 2010/2/6 0:18:00)
- · 一丝不苟的荐析,使古典艺术逐渐融入大众百姓欣赏之列.谢谢..... ( sxpjcgh 发表于 2011/5/20 13:33:00)
- · 优美的旋律~~~~~~~~~ {8/14} {8/57} {8/57} ( 法雨 发表于 2012/8/14 1:22:00)
Copyright @ 2004-2025 www.52jdyy.com 激动社区 - 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yddf
yddf